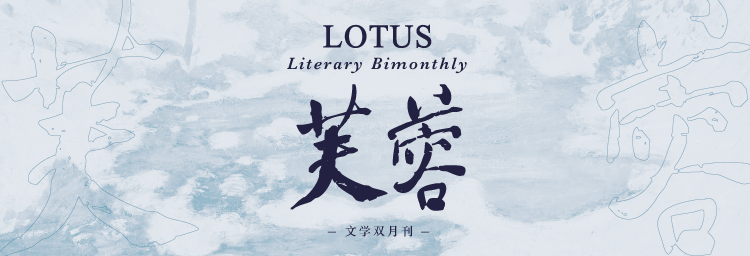

星星索(中篇小說)
文/潘靈
0
遲暮的佳麗畢竟仍是佳麗。百無聊賴酒足飯飽的我,傍晚漫步到廣場時,看見阿誰領舞的頭發勝雪的老太太,心中就生包養網收回了感歎。生平最厭惡廣場舞的我,居然頓足張望起來。一群癡肥的廣場舞年夜媽,被一個身材甚好舞姿綽約的老太太領包養網著,更加像一群養分多餘的老母雞。她們愚笨而生硬的儀態,讓我感到既幽默又為她們肉痛。我甚至以為這老太太是居心的,她居心要扮演殘暴給我看。她皺紋密布的臉上有鶴的自豪。是的,鶴!一只立在雞群里的鶴。皺紋不只沒有絞殺失落她姣好的面龐,還給她增加了飽經風霜卻又超凡脫俗的氣質。一個擁有氣質的老太太,那種美仿佛是從骨子里滲出的,觸目驚心又不可一世。她的臉色安然沉寂,但我仍是感到這里面暗藏著陰險。要不,她為何要與這群廣場舞年夜媽為伍?在我心里,混在雞群里的鶴都是用心叵測的,像美男找襯托人一樣不人性。老太太并不關懷我不懷好意的眼光,她沉醉在廣場舞歡樂得近乎膚淺的旋律里,與年夜媽們一樣,享用著她們律動的幸福。
我了解我這個過客既失望又多余,決議包養網拔腿分開,但走了幾步我卻停住了。我腦海里涌起四個字:素昧平生。對,素昧平生,老太太身上彌漫的美,我很是確認在曩昔是見識過的,但什么時包養辰,我卻怎么也想不起來。我于是又折回頭往,想再做一次看客。但等我回頭,一曲廣場舞正好停止,我與老太太來了個四目絕對。我看到她一臉的驚奇。
是阿水嗎?你真的是阿水?
我從她的聲響里聽出了一個有教化的女人才會有的那種抑制——再高興和受驚也不高聲嚷嚷。我還從這聲響里聽到一種遠遠的熟習,那種低低的悄悄的聲響,跟她叫出的我的奶名一樣親熱。
您是……她的聲響叫醒了我覺醒的記憶,我信口開河,是庹阿姨呀。
阿水!不,該叫你林作家。
庹阿姨!
我們衝動地伸出的手緊握在了一路。
她當真地端詳著我,說一點都沒變。
我說,老了,再過幾年就該退休了。
跟你庹阿姨說老?她松開握我的手,理了理本身的頭發又了解一下狀況我說,你鬢上才染霜,你庹阿姨可是頭上堆雪了。在庹阿姨這里,你永遠是少年。
她邊說邊熱忱地約請我往她家坐坐。看出我有些遲疑,她說,不遠的,就在四周。
我了解謝絕一個白叟的熱忱會不禮貌,就頷首應包養允了。她帶著我走,行動輕快得不像一個年老的白叟。
我庹素曾經很久沒這么興奮過了!看她眉飛色舞的樣子,我的心境也好了起來。我隨著她走出廣場,穿過一條馬路,離開一座有些年月的法度老樓前。病,這裡的風景很美,泉水流淌,靜謐宜人,卻是森林泉水的寶地,沒有福氣的人不能住這樣的地方好地方。”藍玉華認真的
她回身用負疚的眼光看我一眼說,老屋子,沒裝電梯,要光駕你爬樓了。
我昂首看了看這幢黃色彩的法度老屋子,也就六層樓高包養,夾在這高樓林立的古代建筑群中,顯得既矮小又孤單,一種水乳交融的孤單。
我隨著她爬樓梯,一向爬到四樓,腿腳仍然靈活的她看不出有啥費勁,卻是我有些氣喘吁吁。她用鑰匙邊開門邊說,其實有些冷酸粗陋,阿水可不要見笑啊。
房門關閉,我有一種穿越感,恍若進到了20世紀八九十年月的某個城市居平易近家。全部房子的擺設都彰明顯阿誰時期的典範特征。電視機是阿誰時期的,沙發是阿誰時期的,洗衣機和冰箱也是阿包養網誰時期的,獨一分歧的是,在阿誰時期的書桌上,放著一臺比阿誰時期還要遠遠的像一朵喇叭花的留聲機。
房子的擺設固然老舊,但房子卻異常干凈整潔,各類工具也擺放得井井有理。她給我泡了一杯茶,給本身倒了一杯白開水,然后說,聽點音樂?還沒等我頷首說好,她就自顧回身往,抽出了一張老唱片,放在老式留聲機上。
旋律從留聲機的喇叭花口流淌出來,我聽出來了,是《星星索》。
她坐在留聲機前看著我,我也看著她,相顧無言。如許過了好久好久,如許一遍遍地放《星星索》 。
那張老唱片上,就只要這首曲。
是我打破了我們之間的緘默。
庹阿姨,你們家的人呢?
不就在這里嗎?
她邊說邊用手指指本身,隨即關失落了留聲機。她進到臥室,過一會兒抱出來厚厚一摞書和雜志說,阿水,不,林若水作家,我是你的粉絲呀。
我這時看清了,那些都是我出書的書和頒發我作品的刊物。她居然搜集了那么多,讓我心里不知是感謝仍是受驚。
你似乎從不寫你的家鄉,她說,作家怎能不寫本身的家鄉呢?
我不知該如何答覆她的題目,我尋思了一下說,我不是不想寫,是不敢寫。我常常想到家鄉,就會想起你。我想寫你,但又……
寫我?她搖搖頭說,我有啥好寫的?對于你的家鄉白鶴鎮,我只是一個過客,過客罷了。
我搖了搖頭,表現分歧意她的話。
我告知她,家鄉建築白鶴灘巨型電站,白鶴鎮曾經埋在水下了。
她如有所思地址頷首說,也許你是對的。有些工具,它就該像白鶴鎮埋在水里那樣,埋在心里。
我了解話不宜再講下往,便想起身告辭。她看出了我的心思,她說,阿水,再坐一會兒好嗎?
我從她話里不只聽出了懇切,甚至還聽出了央求。
我抬起的屁股從頭回到座位上。屋內,《星星索》的旋律圍繞。
阿水,你三叔此刻還好嗎?我改變頭,驚奇地發明她那張衰老的臉上,有少女般羞怯的紅暈。
三叔?我長嘆一口吻說,他離世都二十年了。
1
白鶴鎮有一段歲月里不叫白鶴鎮,叫白鶴公社,但同鄉們仍是叫它白鶴鎮,習氣成天然,不是說改就能改的。
白鶴鎮沒有白鶴,白鶴鎮處處都是烏鴉。這些黑夜之子,在白鶴鎮上空紛紜揚揚,它們的叫叫讓人心亂如麻。在金沙江邊撐船的我的父親,明天說啥也謝絕干他擺渡的活,他對央求他的顧客們烏青著臉說,沒聞聲烏鴉叫嗎?這是號喪,風波那么年夜,不往對岸會逝世嗎?
這時人們才追蹤關心起了毫無所懼的江風,風確切太年夜了,浪濤把停靠在岸邊的木船都拋到岸上了。
歷經太多風波的船夫父親,他并不是被明天的風波給嚇住了,比如許風高浪急的江面,他見多了。他明天罷工,有另一個隱情,那就是在鎮上教書的三叔回來了。父親想壓服三叔,把我帶往鎮上的黌舍念書。而三叔顯然把我當成了包袱,任父親磨破嘴皮,都沒頷首。
你真忍心看著阿水像我,一輩子在江上提條命討生涯?
二哥,像你有啥欠好呢?船老邁比我這教書匠強。
強?父親吹胡子努目,說林江平呀林江平,你這是站著措辭不腰疼,你吃公眾糧拿公眾錢,做享清福的公眾人,還說我比你強,屁話!你看那些在江岸木棉樹上的烏鴉,個個雙雙鳥眼都瞪著我,恨不得我成水打棒,成它們的牙祭。
二哥,你做的是擺渡活,積善事,上天保佑著你,再說,你那么好的水性,水鬼何如不了你。
江平,古話怎么說,會刀刀上逝世,會水水中亡,這是宿命。
二哥,我幫不了阿水,我學的是吹拉彈唱,可阿水身上沒一丁點音樂細胞。
聽三叔這么說,父親就帶三叔往江邊河灘上。那是我信手涂鴉的處所,沙岸上,是我寫的一些在村小語文課上學的課文。
這字寫得堂堂正正,也許能成我林家光宗耀祖的文明人。
也許是父親的這句話起了感化,也許是我在沙岸上那些在我父親眼里堂堂正正的字感動了三叔,他遲疑了一下,極委曲地應承了上去。
于是,我就如許隨著三叔從江邊的村莊往鎮上。一路上,我心中都覆蓋著激烈的自大,我隨著三叔,那場景像一只驕傲的白日鵝后面跟了一只自慚形穢的丑小鴨。三叔人長得標致、帥氣,這是白鶴鎮處所公認的,我后來接觸到成語玉樹臨風,眼中就呈現三叔的樣子。我一路上都在聽三叔嘀咕,說文明人有啥好,公眾人有啥好。我沒接話,任他的話被江風吹遠。我發明,三叔此次回村來,跟以往分歧。他眉頭緊鎖,一張俊秀的臉緊繃著,像有什么說不清道不明的苦衷。
白鶴鎮上正在趕集,人多得就像白鶴鎮的烏鴉,一個鎮子仿佛隨時有撐炸的風險。金沙江畔熱河谷的太陽既熱且毒,它伸出金晃晃的爪子,等閒就擠出了我一頭油汗。盡管如許,我的心中照舊一片冰冷。我想,三叔必定把我當成了包袱,他的郁郁寡歡和忽忽不樂讓我七上八下,跟如許的晚輩一路生涯,定是我少年時間的至暗時辰。白鶴鎮才不會關懷一個少年的苦衷,它就像一口翻炒著豆子的熱火朝天的鐵鍋,充滿著人聲鼎沸的喧鬧和歡喜。三叔偶然回頭,鐵板一樣的臉上,眼光冰涼地刺我一下,隨即就又回過火往。就在他第四次回頭看我時,黃桷樹上阿誰年夜喇叭響了,那是公社播送站的播送。它一響,喧嘩的鎮子剎時就寧靜了上去。這不是播送時光,大師了解,這喇叭在播送時光之外響起,鎮上必定有工作產生。
播送里播放的是一個攙雜了白鶴方言的說通俗話的女聲,內在的事務居然是一份揭發書。
被揭發的是一個女人,她叫庹素。我熟悉她,她本來是鎮上新華書店的售書員,我曩昔從村莊里來鎮上買連環畫書,常常能見到她。她只需天天翻開新華書店的售書窗,窗前就會擠滿鎮下流里流氣不倫不類的小鎮男青年,他們不是來買書,只是來看她。他們無一破例,都有一種乞丐看到食品的饑餓眼神。個體過火的,還會吹響輕佻而下賤的口哨。但庹素似乎置若罔聞,不聞不問,只是寧靜地賣她的書。她對我尤其好,我叫她庹阿姨,她夸我有禮貌。碰到滯銷的連環畫,她會偷偷為我留下一本,等我趕街的時辰賣給我。
我也愛好睜年夜眼睛看她, 她就像連環畫上那些女的一樣都雅,不!她比她們還都雅。她臉下身上有畫中人沒有的工具,我長年夜后才知那叫氣質。據鎮上的人八卦,說她是印尼回國華裔,她是追隨怙恃回的內陸。在我心里,庹阿姨的樣子容貌,就是仙女的樣子。她不染纖塵,文質彬彬,超凡脫俗,光榮照人。她,配得上任何美妙的描述詞。但后來她調往了供銷社,成了一個賣白糖年夜餅的售貨員。如許的人,也會被揭發,這鎮上套路之深,使我年少的心,只剩下驚詫的份了。
讓我更驚詫得差點失落了下巴的是揭發人。
他居然跟我的三叔有著配合的名字:林江平。
我緊走兩步,對三叔說,三叔,阿誰揭發庹阿姨的人,不克不及跟你叫一樣的名字。
面如土色的三叔冷冷地小聲正告我,這是年夜人們的事,小孩子別摻和。
架在黃桷樹上的年夜喇叭不只理直氣壯,並且帶著惱怒的情感分散出對庹素的揭發。這揭發信里有些語句我要么不懂,要么似懂非懂,我獨一聽清楚的是,深受資產階層腐敗生涯腐化的庹素,企圖用濮上之音和戀愛的糖衣炮彈,籠絡并腐化我鎮的提高青年。她的野心勃勃,是無法未遂的。庹素是一條美男蛇,我們大師尤其是男青年要擦亮眼睛,看清認準她的毒素, 做到拒腐化,永不沾。
有街上混混聽播送里這么講,就聳聳肩自嘲,我想沾,我想被腐化,但沾不上“很好吃,不遜於王阿姨的手藝。”裴母笑瞇瞇的點了點頭。啊!林江平這小子,得了廉價還賣乖,欠揍!
他周遭的人就笑,有人說,湯二毛,林江平得了啥廉價,莫非他把美男蛇睡了?
那倒沒,被叫作湯二毛的人說,據外部靠得住新聞,那叫庹素的美男蛇,在林江平包養的額上親了一口。
不成能!一個用手摸了摸本身額頭的長一張刀臉的小鎮青年說,湯二毛,你別聽林江平吹法螺逼,庹美男吻她?他這種軟蛋,人家看得上他?
這時湯二毛看見了三叔,他手一指對小鎮刀臉青年說,林江平就在那里,你問他往。
小鎮刀臉青年老著方步朝三叔走來,他一臉壞笑說,林江平林教員,美男蛇若何親你的,說給大師聽聽嘛。
世人一陣哄笑,三叔又急又氣,恨不得找條地縫鉆出來。
我這下終于清楚,揭發庹阿姨的,不是他人,恰是我的三叔林江平。這個讓我無法接收的現實,殘暴得像一把包養銳利的尖刀捅進了我的心坎。當氣急廢弛的三叔回身伸手包養網拉我分開這長短之地長短之人群時,我拼命地掙開他的手,討厭而恥辱地跑開了。
2
我發狂地在鎮上攢動的人群中奔馳,樣子像一個偷了他人錢夾被發明的小偷。我一向跑,跑到了鎮上的供銷社的柜臺,包養我了解庹素阿姨在那里賣白糖年夜餅。曩昔,這里歷來都是車水馬龍的,城包養網市擠滿烏鴉一樣黑糊糊的人群。明天這里卻門可羅雀,莫非那烏合之眾,真的把庹阿姨當成了美男蛇?氣喘吁吁的我看著木偶一樣面無臉色的庹阿姨,她站在柜臺前的樣子,照舊楚楚動聽。
庹阿姨!
阿水!
我們簡直是同時召喚了對方。
庹阿姨看著滿頭年夜汗的我,臉上僵硬的臉色柔和了很多,她拉開眼前的抽屜,拿出一本連環畫。《鋼鐵是如何煉成的》,她說,阿水,這本書,是新華書店前兩天剛到的,我替你買了包養一本,我明天不要你的錢,送給你。
她說著從柜臺下面伸出手來,我沒往接她的書,卻牢牢地捉住了她的手。
庹阿姨,我一臉歉意地叫了她一聲,眼淚就奪眶而出了,我嗚咽著說,對不起!
阿水,說啥傻話?庹阿姨說,你沒什么對不起我的呀!
我是替我三叔給你賠不是。
曾經柔和的庹阿姨的臉,又恢復了先前的僵硬,她把書塞我手里說,阿水,那是年夜人的事。
你要好都雅這本書,下次我可要聽你說心得哦。
我說,三叔他……
別說你三叔,庹阿姨悄悄打斷我的話說,假如你見了他,就告知他,我不見怪他。
那全國午,我在街邊用我臨走時母親塞我口袋里的零鈔,買了一碗悲傷涼粉吃后,單獨在街上漫無目標地轉悠,我沒心思看連環畫,也不想回三叔地點的中間黌舍的住處。街上都是關于三叔和庹阿姨的謠言蜚語,那些引車賣漿,毫無所懼地議論著關于他們的風騷佳話。我從那些人的議論中逐步弄清了故事的棱角。
不久前,公社讓鎮上的各單元湊節目,搞中秋晚會。供銷社主任有些難堪,他們社里找不出幾個有文藝細胞的,就往找他的老友中間黌舍校長。校長說,你們庹素,年夜佳麗一個,這不派上用處,豈不資本揮霍?你讓她往臺上一站,唱個歌,保準一片嘩啦啦掌聲。主任感到校長的話在理,就說,這唱歌得有人伴奏。校長說,那好辦,我聲援你。我們的音樂教員林江平,吹拉彈唱,樣樣精曉,全鎮一流。
三叔就如許被校長派往與庹阿姨一起配合節目,兩包養網個邊幅出眾的年青人,一來二往心里都對對方生出了好感,共同也日趨默契。但他們花了很長一段時光都沒挑到彼此滿足的歌曲。
一天,二人又湊一路,聊地利,三叔說本身祖上就是在金沙江上撐船擺渡的。這話提示了庹阿姨,她說,我們唱首船歌吧。三叔說,金沙江上沒有船歌,惡浪滔天的江上擺渡人,一撐船心就提到嗓子眼,還唱什么歌?庹阿姨就說,我說的船歌,是印尼歌。我年夜伯昔時討生涯下南洋,一家人生涯在蘇門答臘群島上,常常聽巴達克人唱。他回國后,教我唱,可難聽了。庹阿姨就哼了幾句,三叔要她鋪開唱。庹阿姨聽了三叔的,就站起身,星星索啊星星索地唱開了。庹阿姨唱完,三叔卻呆住了,愣了好一會兒才把掌鼓得脆脆響,三叔說,太難聽啦!從沒聽過這么難聽的歌,庹素,我愛好你這種唱法,每句前緊后松,柔和而松弛,遲緩而婉轉,有一種揮之不往的憂傷,仿佛在表達懷念之情。三叔的話,讓庹素也高興得興起掌來,她衝動地說,不愧是白鶴鎮的音樂佳人,江平,你解讀得太到位了!聽我年夜伯說,巴達克人唱的就是懷念,他們歌頌的是戀愛。
戀愛這兩個字一出口,庹素臉上出現了紅暈,三叔也弄了一張婿家也窮得不行,萬一他能做到呢?不開鍋?他們藍家絕對不會讓自己的女兒和女婿過著挨餓的生活而置之包養網不理的吧?年夜紅臉。
三叔吞吞吐吐地說, 愛……戀愛?中秋晚會上唱這歌適合嗎?
庹阿姨說,怎么分歧適?我聽年夜伯說,在蘇門答臘群島上,巴達克人的歌年夜多是歌頌戀愛的呀!他們年夜慷慨方唱,男女老小都唱,那排場美妙得很。
可……三叔猶豫了一下說,這是白鶴鎮呀。
庹阿姨撒嬌似的說,我不論,我就只想唱包養網它,我要和你一路唱它包養網。
唱它?三叔說,我連這首歌的歌名都不了解。
庹阿姨說,它就叫《星星索》。
《星星索》?三叔搔了搔頭發說,好怪的歌名。
庹阿姨說,我昔時也跟你一樣感到怪,年夜伯就說明,說那是巴達克人的船槳有節拍升降在水面上收回的聲響,星星索,星星索。
好吧,三叔說,就隨你的意,歸正大師都不了解印尼話,不會懂它的意思的。
三叔一應允,庹阿姨就衝動得蹦了起來,她在三叔額頭親了一口,就像一只歡樂又害臊的羚羊跑出了房子……
中秋晚會上,三叔和庹阿姨的男女對唱《星星索》,在白鶴鎮惹起了顫動。
3
一首《星星索》,仿佛是一粒石子投進一片靜寂的湖面普通,在白鶴鎮人心中蕩起了漣漪。人們固然聽不懂這對金童玉女唱的是什么,但旋律仍是從耳膜鉆進了他們荒涼而干涸的心坎。很舒暢,很難聽,生硬的時間包養似乎都變得柔嫩起來——白鶴鎮的人們,心中有了直接而異常的感觸感染。
鎮上的年青人,被這首來自異域的歌給迷住了。中間黌舍的年青教員,自是不會放過近水樓臺的機遇,他們圍著我的三叔林江平,要他教他們唱。豐年輕教員還提了酒,上門往找林江平,打算從他嘴里套出些關于這首歌的內在的事務和信息。但三叔卻老是笑而不答。終于有一天,三叔在他的年青同事包養網心懷叵測的幾次勸酒下,道出了這首歌的“秘密”。
三叔借著酒勁揮動著手說,這首歌頌的是戀愛!
三叔的話,說它是默默無聞也不為過,那些三叔的年青同事面面相覷,臉熱情跳,十足選擇了沉默不言,然后自顧散往了。
在不談愛的年包養網月,戀愛是一個禁詞,三叔沒有把它關在牙齒的樊籠里,他吐出了它,等于吐出了禍水。
匿名的起訴信就到了公社主任的手上。中秋晚會上在稠人廣眾之下唱戀愛歌曲,這還了得!
兩個輕舉妄動的年青人,讓公社主任很是末路火,他感到事態額外嚴重,于是就叫人請來了中間黌舍的校長。校長也感到事態嚴重,但他以為林江平是被蒙蔽了。
我包管他不懂印尼語,校長當著主任的面拍著胸脯說,始作俑者定是庹素。
主任說,但唱的是戀愛可是你的教員林江平說的。
那也是庹素教的,校長說,聽說她有海內關系。她明知歌詞內在的事務關于戀愛,卻還要在中秋晚會上唱,這念包養網頭可疑呀。
主任頷首,說庹素確有海內關系,不免受腐敗思惟影響,唱濮上之音,事出有因,但林江平隨著瞎起哄干啥?了解是男歡女愛,還唱?
校長想了想說,他中了庹素的毒,據青年教員反應,他倆此刻打得非常熱絡,暗裡里約會。這都怪我,客不雅上起了撮合的感化,好端端一個青年包養教員,中了無孔不進的資產階層的毒包養。
要拯救他,主任招招手說,掃帚不到,塵埃不會本身跑失落,該替他掃除一下思惟衛生了。
那天的傍晚,白鶴鎮上沒有其他的話題,連江風的呢喃,仿佛都是在交頭接耳林江溫和庹素這對男女。我聞聲鎮東口白鶴飯館里靠窗的一個飲酒的漢子用高亢的嗓子對他的酒友講,林江平不是工具,軟蛋一個,他還不如黃廷波。黃廷波固然壞,但人家有擔負。我們都了解那庹美男給黃廷波看的是《簡·愛》,仍是繁體字的,有人告發后,公社主任帶著審查組,找黃廷波談了三天三夜,人家黃廷波就是咬逝世,說庹美男借給他的是《水滸傳》。
酒友們都頷首稱是。此中一個用筷子敲擊著酒碗一臉暗昧地說,這黃廷波如果一無可取,會吸引庹美男,他成天往庹美男的房子跑,一往一兩個小時。
嗓子高亢的漢子說,一朵鮮花插牛糞上,不說也罷。
用筷子敲酒碗的那位持續懶洋洋敲了幾下說,曩昔認為黃廷波是牛糞,此刻看來,林江平更是,他空長了一身好皮郛,沒點漢子氣。
我聽這群醉翁八卦三叔,恨不得沖進店往揍他們。但我了解本身勢單力薄,他們會像提一只雞仔一樣把我從酒館里扔出來。我了解,我像本身的三叔一樣脆弱。這讓我少年的心坎恥辱極了。
我此刻了解,庹阿姨為何會從鎮上的新華書店調往供銷社了,本來是她借書給黃廷波。阿誰人我熟悉,長得魁偉強健。他是公社的一名干部,做什么都出手輕下手狠。鎮上的人背後里說,這黃廷波的心不是肉長的,而是鐵鑄的。有人還傳,說他從誕生就得了一種病,不了解痛苦悲傷是什么。
在我少年的記憶里,假如有魔鬼,那必定是黃廷波的樣子。庹阿姨會借書給黃廷波,這是我千萬沒想到的。那叫《簡·愛》的書,究竟是本如何的書?我的心中,一會兒多了很多多少題目。
我那天在街上,替三叔感觸感染了太多的恥辱,直到夜色濃烈,才極不情愿地回到三叔地點的中間黌舍教職工宿舍。我排闥進屋,聞到了刺鼻的酒味。三叔一小我喝悶酒,他喝高了,像一攤爛泥龜縮在床角,手中握著一個空酒瓶,衣服上,沾著令人惡心的包養吐逆物。他見我出去,想爬起來,但還沒等站起來,就像年夜風中搖擺的樹又倒下了。他醉眼蒙眬地看著我,抬了抬他精神煥發的右手,口齒不清地沖我嚷開了。我驚駭地看著一個醉漢惱怒的樣子,費了好年夜勁才聽清楚他在吶喊什么。
三叔在問——我包養網不知他在問誰——不是給我包管過,只需我說出實情,就饒了我們嗎?啊?
我想,阿誰“我們”,該是他和庹阿姨。
我走到床角,費勁地把他扶起來,搖搖擺晃的他把包養難聞的酒氣噴了我一頭一臉,他還在口齒不清地問,不是包管過嗎?為啥措辭不算數呢?
我把他扶到床上,給他脫衣,蓋好被子,然后往清算吐逆物。天天渴望長成年夜人的我,第一次對成人世界佈滿了膽怯。
(原載于2023年第3期《芙蓉》潘靈的中篇小說《星星索》包養網)

潘靈,男,布依族,1966年7月生于云南巧家,1988年結業于云南師范年夜學教導系。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云南省作家協會副主席、邊境文學雜志社社長兼總編纂、享用國務院當局特別補助專家、中宣部全國文明名家暨“四個一批”人才。作品屢次被《新漢文摘包養網》《小說選刊》《中篇小說選刊》轉錄發載。出書有長篇小說《泥太陽》《翡熱翠冷》《血戀包養》《情逝》《紅鷂子》,小說集《風吹雪》《奔馳的木頭》《承平有象》等。獲第十屆全國多數平易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云南文學獎一等獎、《小說選刊》年度年夜獎、《平易近族文學》年度年夜獎等。